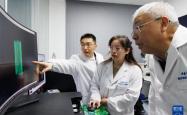专访天翎科CEO蒋彬:eVTOL将走向全倾转|低空经济21人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孙燕 上海报道

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
近日,全球第一架全尺寸倾转涵道翼eVTOL——天翎科L600亮相。
作为国内第一家采用全涵道设计的eVTOL企业,天翎科在中国eVTOL赛道上扮演了独特且具有前瞻性的角色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
5年前,当资本和市场都偏爱更快出成果的复合翼或多旋翼时,刚刚启动整机开发的蒋彬毅然坚持其选择。5年来,看起来简单却并不能很快成功的技术发展不断证明混动、全倾转、全涵道构型的可行性:电池能量密度不再“狂飙”,首款国产混动航空发动机即将获颁型号合格证、生产许可证,全倾转、全涵道构型的可行性也得到了验证。
时至今日,当市场逐渐从“能飞”转向“好用”,对噪音、效率、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时,天翎科当年的独特选择,逐渐转化为其核心竞争壁垒。
近日,天翎科创始人兼CEO蒋彬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。蒋彬回忆道,2020年天翎科团队确定了技术路线和场景,明确初始场景一定要做高性能飞行器来与传统航空器竞争,终极城市场景需要低环境影响航空器来满足大规模运行要求。但对于如何实现两者的统一,团队经历了很多尝试和修改。“我们共设计了5个构型,每个构型都造了缩比机、进行了试飞,不断迭代出了今天的构型。”
蒋彬认为,对于未来技术方向、场景的判断,都会反映在eVTOL构型上。“用途、场景在前牵引,技术发展在后推动,场景、技术发展方向都找对了,一定能走到彼岸。”

一代动力,一代飞行器
《21世纪》:在通用航空领域你有长达15年的研发和全球适航工作经验,如何看待此前中国通航产业的发展?
蒋彬:之前通用航空在中国发展得不太顺利。从飞行器自身来看:飞行器大规模运行需要“双保险”,一方面飞行器本身要好用、安全,另一方面监管方要有足够的手段对航空器进行有效的控制。
但过去,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国家的航空器。由于制造商对其核心技术(如电磁环境、设计算法)甚至飞行记录数据都严格保密,这些航空器对中国监管机构而言是技术上的“黑盒子”。因此中国民航局建立并执行了一套覆盖飞行员、维护、运行和空域管理的严格监管体系,以确保万无一失,但成本高昂无法大规模运行。就像如今相关部门对正规企业无人机有反制手段,是因为中国无人机企业可以更好地与监管方合作,使得监管当局有更多的管理手段。
一代动力,一代飞行器。随着新型动力装置出现,中国一下子有了和美国、欧洲相同的设计基础,也就有了同场竞技的资本。一方面,中国的主机厂可以通过设计体系、仿真、试飞等过程证明eVTOL的安全,另一方面通过与监管方的深度合作,监管方也得到了监管eVTOL的手段。主机厂和监管方一起成长,能够实现“双保险”。
《21世纪》:为什么中国主机厂都是最近几年一起成长起来的?
蒋彬:从过去100年的飞行器发展过程看,“一代动力,一代飞行器”是通用规律。电机的出现,启动了这一轮动力革命,全球所有国家再次站上同一起跑线。
电机和内燃机的本质区别在于,电机是尺寸无关的。假如需要1000kW功率,可以做1个1000kW的电机,也可以做10个100kW的电机,两种方案的综合效率、电机重量、电机大小差别不大。而若是用1000kW的航空发动机,热效率可以达到40%;但分成10个100kW的发动机时,热效率仅有20%左右,重量却比单发动机方案重50%以上。
飞行器设计随动力特点而改变。由于电机具有尺寸无关特性,飞行器可以做分布式动力系统,也可以把机翼和动力融合到一起——这能够结合机翼形状,优化推力、升力特性。
少有人走的路
《21世纪》:天翎科2020年开始研发倾转涵道翼eVTOL,为何选择这一独特构型?
蒋彬:天翎科2023年成立,核心团队从2020年开始做eVTOL整机开发。我们在设计飞行器时,考虑到了短、中、长期的落地场景。短期之内,我们要替代现有的直升机、小飞机,因此飞行器的高性能、低成本,是第一阶段能够产生商业价值的必要条件。中长期来看,eVTOL要进入城市环境中大规模运行,需要更多考虑机外的人员,因此公众安全、噪声影响是eVTOL规模化的核心。我们认为,倾转涵道翼是无论短期、长期都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构型。
倾转涵道构型诞生于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。当时,美国海军给贝尔公司提出了一个需求,要求开发一种能在航母甲板等狭小空间垂直起降、具备固定翼飞机速度和续航的V/STOL(垂直/短距起降)飞机。根据这一要求,贝尔设计出了首款倾转涵道翼飞机——X-22。
X-22已经验证了倾转涵道构型的气动特性,但当时无法大规模商用。这是因为,它采用四个可倾转涵道风扇,各自需要一台发动机驱动,经济性较差,系统交联也较为复杂。而随着动力系统的革命,如今能够用一串电机取代原来的发动机,以更低的成本解决了当年的商用化难题,同时继承了速度快、操控稳定等构型优势。
《21世纪》:同为全涵道构型,为什么Lilium早早起步,却沦落到破产、被收购的境地?
蒋彬:从技术层面看,Lilium错判了技术发展路径。2016年Lilium的构型和天翎科一样,但后来改变了。
其背景是:2016年至2020年,电池能量密度以年均30%的速度突飞猛进。Lilium预估电池会继续保持这一增速,到2025年功率密度、能量密度都将翻3倍以上,因此在2018年修订了构型。
但随着电池体系接近其理论能量密度上限,2020年以后,高功率电池的能量密度的年均增长速度明显放缓,回落到3%-5%的水平。
举个例子:2020年我们团队研发1/2缩比飞机时,单体电芯的能量密度已经能够达到275Wh/kg。目前天翎科用的高安全水平电芯能量密度基本没有变化。
《21世纪》:L600搭载了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,天翎科为何选择增程?
蒋彬:eVTOL在不同飞行姿态下的需求不同:垂直起降阶段需要高功率,巡航阶段需要高能量。而电的优势在于高功率,油的优势在于高能量,增程式混动能够发挥两种能量系统的优势——起降阶段纯电驱动,平飞阶段烧油发电、由电驱动。
eVTOL垂直起降,类似于汽车起步,汽车起步同样由电机主导。电机在低速(甚至零转速)时就能输出最大扭矩,把eVTOL托起来;而发动机的燃料虽然蕴含巨大能量,但其单位时间内将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的速率(即功率)受到了限制。因此,eVTOL起降阶段由电机主导,是物理事实决定的。
增程式混动系统由发动机和发电机组合而成。发动机方面,我们用的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(608所)产品,608有国内唯一认证的航发产品,也是中国首款明确设计上就预留了“混动化”接口的国产航空发动机。
考虑到平飞300公里/小时所需的能量消耗,我们匹配了一个完全满足平飞功率的增程器。电池则是预留给垂直起降和应急用的:电池能够保证平飞100多公里或者6次垂直起降,确保在发动机出现问题时安全达到。

技术、场景决定构型
《21世纪》:市面上的载人eVTOL还有2座、4座、5座等设计,L600采用六座设计有哪些考量?
蒋彬:首先,我们非常明确的是前排一定要设置双座。
我们最早定前排双座时业界普遍不认同,但如今很多友商都已从前排单座改成前排双座。Joby出于构型考虑,其6个倾转旋翼挤压了机舱前部的可用空间,导致物理上前排无法并排布置两个座位。虽然坚持前排单座,但Joby需要投入巨资研发高保真飞行模拟器,这是用培训高性能军用飞机(如F-35战斗机)飞行员的方式培训民用飞机驾驶员,成本高昂。
天翎科之所以坚持双座,是出于短期培训、长期运营的综合考虑。短期来看,eVTOL仍将按照传统航空器规则运行,前排一定要双座才能培训;早期飞行也可能需要配备正、副驾驶员。而在航空器可以自主飞行的未来,乘客也不会选择一个人坐在前排,而是倾向于两人并座交流。
其次,我们的构型决定了我们的超长客舱。串列翼飞行器不同于其他所有飞行器,由于前翼和主翼需要留出足够长的间隔距离,这导致客舱很长。L600客舱其实有8座的空间,布局载人、载货都比较容易。
大客舱对于未来发展也很有意义。假设电池能量密度以每年3%的速度增长,那么每年可以节省21公斤,5年就能省下一个成年人的重量;而可能5年后eVTOL将真正开始规模化运行,到时候可以再增加1到2个座位。
《21世纪》:载荷和航速,主要取决于电池技术进步吗?
蒋彬:所有的部件都在进步。主机厂必须为技术进步预留空间,让eVTOL有能力飞得越来越快,也有能力布局更多座位。
我们选择全倾转涵道翼构型,也出于这一考虑。当推进技术越来越成熟,要求eVTOL飞得越来越快时,非全倾转构型的速度很难提升。
只要在低速飞机(最高速度可以达到463km/h)档位,所有认证条件几乎相同。L600的最高飞行速度是360km/h,还有100km/h的进步空间;电池持续、缓慢的进步也可能发挥客舱空间的优势,可以从6座升级到8座。所以,L600在未来10年会越来越完美。
《21世纪》:据统计,目前eVTOL的构型有1000多种。你觉得技术路线会朝什么方向收敛?
蒋彬:按照“一代动力,一代飞行器”的观点,如今的电动航空行业相当于1940年-1960年。当活塞式内燃机转变为涡轮式发动机,千奇百怪的飞行器随之出现:有的主机厂把发动机放在机舱里,有的放在背上,还有的放在翅膀中间、尖上……直至1960年前后,翼下吊挂发动机布局被证明是喷气式客机设计的最优解,并一直延续至今。
收敛的方向一是要满足场景的要求,二是要满足技术发展的规律。
电机出现后,千奇百怪的eVTOL随之而来。短期来看eVTOL的飞行性能必须打败传统航空器,接管现有场景,否则没有理由进入eVTOL时代。所以高性能是必然。高性能也就需要高航速和长航程,即全倾转和混动。长期看eVTOL要大规模运行,需要公众接受每天有大量的航空器在附近运行,那就意味着低噪声和高安全,特别是对飞机外人员的安全防护,这一点涵道有天然的优势。
《21世纪》:这一共识基于什么达成?
蒋彬:基于物理和运行场景要求。物理限制一直存在,之前大家觉得可以开创新场景。
所谓新场景,包括以eVTOL为低空文旅的载体。现在依然有这样的说法,但大家已经不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大规模运行的场景。因为若把eVTOL飞行当作文旅项目,意味着这是一个猎奇的产品,也意味着产品数量少,无法规模运行。
美国、欧洲一直强调,未来先进空中交通的运行法规仍然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第91部(Part 91)和第135部(Part 135),未来的运行场景仍然是通勤、应急等91部和135部规定的场景。
也是经过这几年百花齐放,大家发现过去100多年没有创造出来的场景,未来10-15年内也不会出现。创造场景比创造技术更难,不如用新技术解决老场景的问题,先打败过去才有未来。
逐步接近最终场景
《21世纪》:对于应用场景,天翎科有怎样规划和部署?
蒋彬:第一步是低成本替代现有的通航飞机。比如救援直升机的最快飞行速度是220km/h,L600最快能飞360km/h,不仅节约成本,而且在及时性、舒适性、安全性上全面碾压。
这意味着,我们能够把通航飞机市场从原来的1000架做到1万架。通过1万架eVTOL积累100万以上小时飞行经验,能够证明eVTOL比传统通用航空器更安全,底层也能够让监管方有手段可监管,那时候我们将创造新的场景——城市空中交通(Urban Air Mobility,简称UAM),eVTOL将在城市大规模运行。
《21世纪》:在大规模运行之前,天翎科计划如何盈利?
蒋彬:主要是从通用航空市场分蛋糕。目前通航市场包括应急救援、载人商务出行、短途运输、短途通勤等,我们目前在中国西南、西北地区和中东、东南亚等地都有一些意向订单。
我们希望L600全生命周期都能产生价值。预计L600完成服役后,我们将用其改装无人货运机,飞机本身的采购成本几乎为0。
《21世纪》:L600能够实现全生命周期运营成本为每公里每个座位1.5元,在载人eVTOL行业处于什么样的水平?
蒋彬:这在混动eVTOL中处于平均水平,但比纯电eVTOL便宜很多。
这是因为有电池更换成本。电动航空比电动汽车更换电池要频繁得多:汽车电池在材料选择上较为保守,且工况好,可以在几千个循环后更换电池;航空电池的材料选择相对激进,一般在500-700个循环后就要更换电池。
按此测算,eVTOL每次起降所对应的电池损耗成本约为1000元。
L600由于有混动系统,充一次电可以起降6次——每次仅用5%的电量起降,起降6次后还余40%电量。而如果L600是纯电动力,每公里每个座位将高达6元——电池更换的成本,远远高于燃油成本加上发动机大修成本。